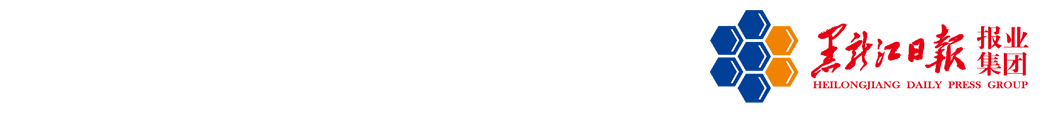□林小仲
我下乡九年,上世纪七十年代,齐齐哈尔市火车站是我往返北和阿荣旗的必经之地。齐齐哈尔是我国北方重工业城市,春节后的火车站挤满了返乡的京津沪各大城市的知青们,这群数十万闯关东的大孩子们,齐齐哈尔以卧龙自然保护区的丹顶鹤闻名于世,知青成为冰雪覆盖的丹顶鹤故乡的又一道风景线。

作者林小仲
记不清楚,那列67次,还是68次列车,从北京发往齐齐哈尔的绿皮火车,夜晚从北京站发车,见站就停,历经三十多个小时左右,深更半夜停靠齐市火车站。无论是转往嫩江各地农场(兵团),还是返回呼伦贝尔的知青们,大都要在齐市火车站候车大厅木结构长椅混上一宿,等待天亮后再去转车。
候车大厅挤满了人,那年月,在黑龙江知青与老乡很容易区别,知青们大都青春年少,衣着蓝色的衣服,或者形形色色的旧军装,栽绒帽,而老乡们年纪老少皆有,多是黑布裤袱,羊皮大衣,狗皮帽。我斜卧在冰凉的木长椅上,被一阵吵闹声惊醒。在信息不畅,少有娱乐设施的岁月,看热闹是我们那代人的一大特点。挤过去一看,几位天津知青与一伙上海知青为抢椅子发生争执,双方剑拔弩张,为首脸庞白净带眼镜的上海知青嗓门很大,夹杂方言的普通话,慷慨激昂,而几位天津男知青,话不多,却跃跃欲试,象《智取威虎山》中杨子荣一样,冲在前面男知青戴一顶狐狸皮帽,虎背熊腰,若不是几位天津女知青拉住,看来一场群架难以避免。忽然听到一声响亮的声音断喝,标准的北京口音:“你们吃饱撑的?都混成这样了,还好意思为抢椅子打架,都是知青,哥几个有什么过不去的?”我望去,一米八几身材魁梧的大个子,身着国防绿军大衣,他是我们邻村北京知青老贺,几句话就将两拨人无名火浇灭。在老贺提议下,京津沪三伙知青,二十来个人将几张长椅拉到一起,团团围坐。老贺从手提包中拎出一瓶牛栏山二锅头,用牙咬开盖,倒在写有“广阔天地,大有作为”的知青瓷缸子中,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三地知青,你一口我一口传递白酒下肚,霎间无拘束相互介绍起来。
那伙上海知青下乡在大兴安岭黑河地区,为首的眼镜出身书香门第,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都成了被扫地出门的臭老九,几次推荐上大学和进厂矿都没有他的份,他身边还有两个跟他一起从上海探家归来的弟弟,当年他们跟哥哥到黑龙江下乡时,只有14、5岁。他叹气道,在这里修理地球,也比在上海里弄中看邻居们的白眼,听他们大批判的风凉话好。天津几位知青都下乡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牧区,受马背民族影响性格豪放,为首带狐狸皮帽子那位健壮豪爽,他身边小鸟依人的女知青是他的女朋友,漂亮清纯的她,聊到在天津无依无靠的爷爷奶奶,她眼里充满泪水,她的父母是医生,随626医疗队去遥远边疆公社卫生院长住,不知那年能再回天津。她的两个哥哥,分别到山西晋南和河北承德下乡。
渐渐候车室里有许多各地知青向这群人靠拢,有人插话,更多人在旁边静静的听,在讲出身株连的时代,大家的境遇大同小异。家境好、有门路的知青,下乡不过蜻蜓点水,早就招兵、招工,或工农兵学员招生走了。我也了解老贺的情况,他在北京翠微路部队大院长大,浩劫年代,开囯将军的父亲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审查,母亲被发往部机关在河南的五七干校,哈军工毕业的大哥被从部队转业,年幼的弟弟妹妹在北京家中留守,无人照料。老贺若有所思,只是在倾听别人诉说,他一根烟接一根烟抽。忽然,他问我为什么这么早就回阿荣旗,我告诉他,北京越来越漠生了,那里的万家灯火似乎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。老贺笑着说,兄弟别那么悲观,慢慢熬着,日子还长呢?
为了打发齐齐哈尔候车大厅寒冷漫长的冬夜,不知谁提议,唱起知青们喜欢的歌,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、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、《草原晨曲》、《横断山路难行》等,仿佛大家又回到金色的学生时代。《南京知青之歌》:“蓝蓝的天上,白云在飞翔,美丽的扬子江畔,是可爱的南京古城,我的家乡。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,曲折又漫长。生活的脚印,深印在偏僻的异乡”。这是南京知青任毅险些付出生命写下的知青之歌,歌声悠扬低沉,却充满人性的哲理,他不仅是南京知青的思乡曲,也是所有城镇下乡知青的思乡曲。多少年后,关于上山下乡运动,青春无悔和有悔争执不断,然而,对于当年一千七百万知青而言,“我们要回家”这句话应该是绝大多数知青的共同想法。没有这种体验的人,很难找到这种感受,不了解这一点,去点评那场运动都是瞎扯。
说着、唱着,东方鱼肚白,大家依依不舍,握手道别,奔向各自返回乡村(农场)长途汽车站。多少年过去了,齐齐哈尔火车站候车大厅那个难忘的夜晚的故事依然历历在目,再未重逢相遇的朋友们,你们返城的后知青时代日子里可好。
2019年10月25日于纽村
本文作者为呼伦贝尔阿荣旗北京知青
摘自《北大荒知青网》
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版权所有